记忆里无数个清晨,我家那栋老房子聚集了邻近的老妪们。晨曦透过木板的罅隙洒泄一些海棠粉的气息,在空中飘摇零落,刺激着我海马回里的海绵体。
客厅桌上一块红布摊开着,摆满玉镯、玉坠、甚至璞玉,偶尔还有玉扳指。然而未必全是翠绿色成品,有时也夹杂一些白色、黄色或粉色的玉,名字我倒弄不清,只知道老人家捧在手心,又怕弄疼;揣在怀里,又怕捂着了的那种神情,深深地嵌在我小小的心灵里。
ADVERTISEMENT
长辈们梳发髻者居多,一位平日深居简出的缠脚老太,也在孙女的搀扶下,赶来凑热闹。她们穿着旧式的服装,把脖子紧紧地扣在衣领里。几粒小盘扣将民初的旧风与南洋的海风划分开来。她们亲手熬制的浆糊把上衣浆得直挺挺的,谁也不比谁逊色。大伙儿用心地挑选着心里头上等的美玉,掂量着它传家的价值,评估着家乡的讯息。一块玉,承载着望眼欲穿的故乡,飘洋过海地把乡土气息也一并递送过来。此生再也无法魂归故土的心思就此摄住在玉里,留待后世缅怀。
曾祖母好客,加上母亲拿手的红桃粿,外送一壶铁观音的款待,我家自然成为最理想的聚会场所。隔壁老妇胆识过人,南来途中丧偶丧子,但既然搭上了一趟没有回头路的船,只好一路走到底。擦干了泪水,她常年往返中马两国,充当信使、跑腿,也攒一点零头防老。人称“杯子”的老妇就像一艘两头都靠不到岸的小船。蕉风椰雨的嘱咐夹着咸味,行李箱里满载着期盼与歆羡,随着她飘荡在马六甲海峡的浪涛中。季候风一起,她又再次启航,带回故乡的余温,哪怕只是捎上只言片语。
她让我年幼的心里镶嵌了耆老们口中的“唐山”,知道海峡望不见的那头还有亲情的枷锁。那时候的我说得一口标准的潮州话,上学时老师不厌其烦地纠正,最后也只能抓狂地弃械投降。那一场场聚会,它甚少是欢乐收场。几乎每位老人家怀里都揣着一条浸染了满酱缸心事的手帕。一班姊妹欲语还休,未语泪先流。她们交换着记忆底鲜活的人事物,一枚玉镯放在日头下仔细端倪,望的不是渣质,而是远方无远弗届的召唤。
我也有一只玉手镯,曾祖母把它留给了我,距今已过一世纪。她是大户人家的千金,陪嫁的首饰仅剩这玉手镯未被变卖。高堂的祝福与期许、战火的洗涤、家园尽毁、孩子离散……过往像停滞不前的尘埃粒子,凿进了这只手镯里。今天握在手心里的这只手镯虽有血泪的润饰,却早已粗糙不堪。
孩子说这是古董,要把它卖了吗?卖?我把玉手镯凑到鼻头,一股海棠粉味淡淡地输送进来,我仿佛望见踽踽独行的曾祖母走进了红墙碧瓦的大院里,隐身而去了…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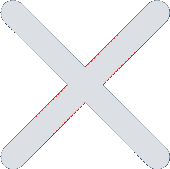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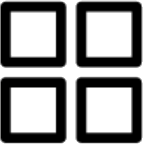
ADVERTISEMENT
热门新闻





百格视频





ADVERTISEMENT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